夏寧
近期火爆出圈的Labubu,非常可愛地站在了全球時尚潮玩圈的鎂光燈下,一些國家的泡泡瑪特線下店發售時甚至出現搶購者為購買而發生了“肢體沖突”;網友們在微信朋友圈紛紛曬出自己的Labubu,有的是之前買入,彼時尚不知這就是大名鼎鼎的Labubu,而此時已為之傾倒……
在此背景下,閱讀由格致出版社出版的《心愛之物》正當其時。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人阿倫·阿胡維亞(Aaron Ahuvia),是一位營銷學教授,品牌摯愛概念的提出者,譯者為譚詠風。阿胡維亞雖是營銷學教授,但是他對心愛之物的解讀,并非單純從營銷的角度,而是為人們提供了心理學、社會學方面的視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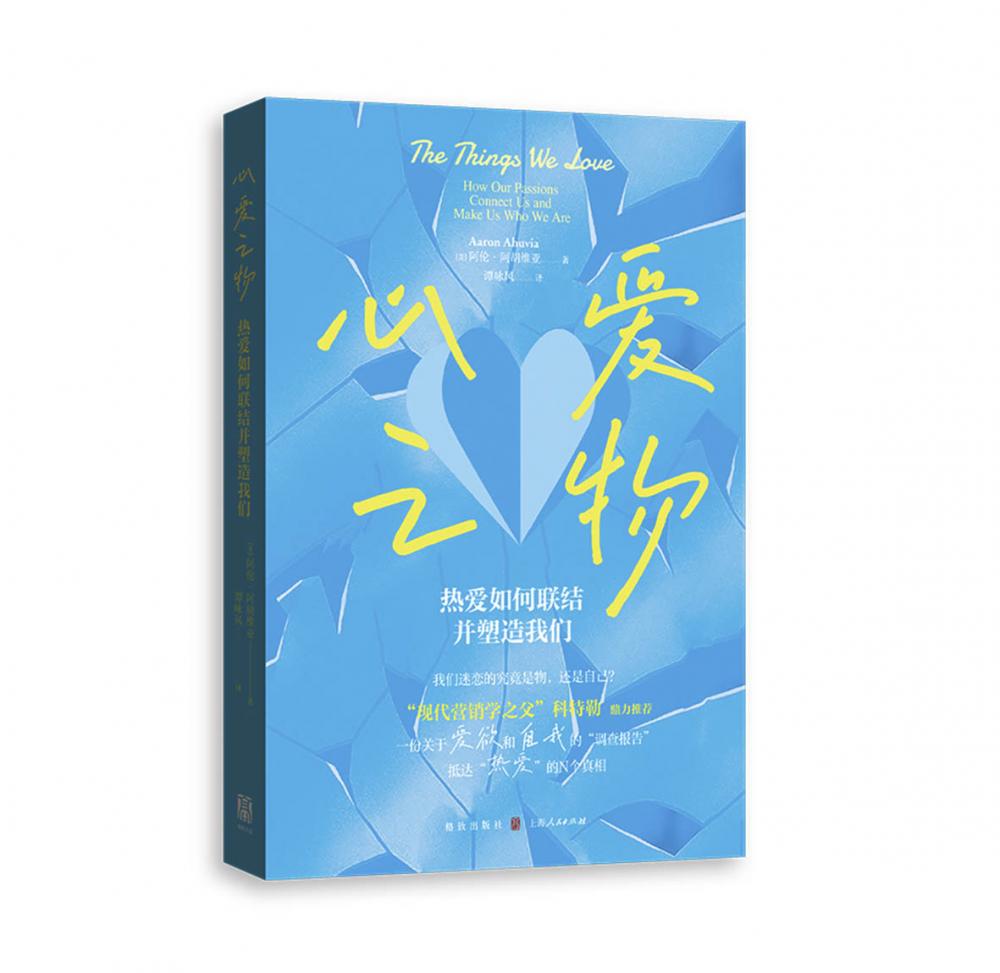
該書對愛物做了一些必要的“澄清”,認為愛物不等同于物化,愛物也不是一種缺陷,而是人類幾萬年前進化出來的一個功能。書中指出,根據考古學家的發現,人類在5萬年前就進化出了愛物的特征和功能,而4萬年前的人類就擁有了大量藝術品。這些藝術品中包括人像,它們是高度擬人化的物品,是“愛的最佳候選”。可見,愛物并不是物質主義社會發展出來的特征,而本身就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特征。
當然,愛物的目的最終會回到人身上。作者對人與物的關系的闡釋令人印象深刻,他認為,人喜歡心愛之物,并不一定是物化,“人-物”的關系最終會回到人,即實際上是“人—物—人”的關系。即使我們與事物建立聯系,我們的大腦也會優先考慮人。因為我們始終具有一種叫“社會性”的特征。正所謂,人是社會化的“物種”。
有兩個例子有助于解釋,人們之所以愛一種物,可能是出于一種社會或身份認同。人們經由愛物來探索自己,正所謂“乘物以游心”。一個例子是,新加坡某些地方的人對勞力士手表十分喜愛,認為這是一種成功的象征。同時,勞力士手表也極具投資性,因此得到了人們的青睞。雖然愛物,但其中蘊含了一種身份象征(成功群體)與功能價值(兼具投資)。由此可見,人們愛物,最終還是回到了人的層面。
這無疑會給營銷帶來靈感。喜愛某件事物的主要驅動力是將其視為自己身份認同的一部分,高端品牌利用這些廣告來建立一種觀念,即它們品牌的目標消費者正在努力實現這種身份認同。
另一個關于愛和群體認同的例子,是雀巢咖啡的營銷案例。這是一個上世紀的例子,雖然古老但很有啟發性。它告訴我們,人們愛一些物,有時可能并不是從心里真的喜歡它,而是源于一種身份群體認同。雀巢速溶咖啡曾一度銷售不暢,雀巢公司不解,于是找來了專家做研究。研究結果發現,一些女士雖然覺得雀巢速溶咖啡的味道也還不錯,但內心卻覺得速溶咖啡應該是那些慵懶、懶惰的人喝的。因為在她們心目中,那些勤快、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條的主婦是肯定有時間和條件為丈夫和家庭煮一杯現煮咖啡的。
可見,在產品的銷售中,并不僅僅是簡單的賣貨,以及“酒香不怕巷子深”,其中蘊含著的身份認同也是何其重要。這種身份認同會直接影響到如何開展營銷工作,廣告策劃創意等。如果你是正在做營銷、廣告、策劃工作的,或是有志于這些方面工作的,不妨一讀。
當然,人們喜歡心愛之物,也存在著一種“浪漫之愛”。我們與所愛事物之間也會發生某種化學反應,這種化學反應歸根結底就是我們是否享受與心愛之物相處的時光,因為物經常可以為人提供內在和外在獎勵。舉個例子,一個愛車的人喜歡駕駛汽車給自己帶來的樂趣與愉悅感(內在獎勵),同時駕車也保證了這位車主準時通勤上班(外在獎勵),作者認為外在獎勵會增強內在獎勵的效果。
非物質主義的愛物,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建立親密關系而轉投自己愛的物。這或許可以部分解釋為什么當下養寵物的人越來越多,寵物經濟甚至成了一種越來越耀眼的經濟現象。當然,作者也很友善地在開篇就解釋道,在本書中,“事物”這個詞也包括了動物,在這里要首先請求動物愛好者朋友們的原諒,之所以把動物也叫事物,僅僅是因為想要在書中便于討論,如果寫成“我們對事物和動物的愛”,那就有點冗長了。
或許,人們對Labubu的喜愛,也源于此,當然還有其他心理方面的原因,比如開盲盒心理、炫耀性消費等等,在此不贅述。

















